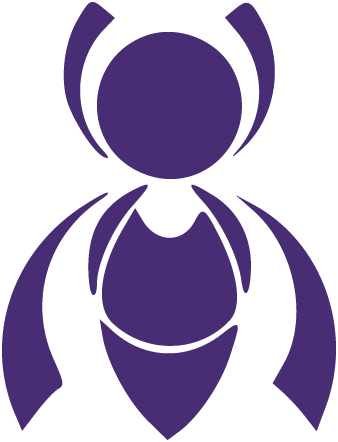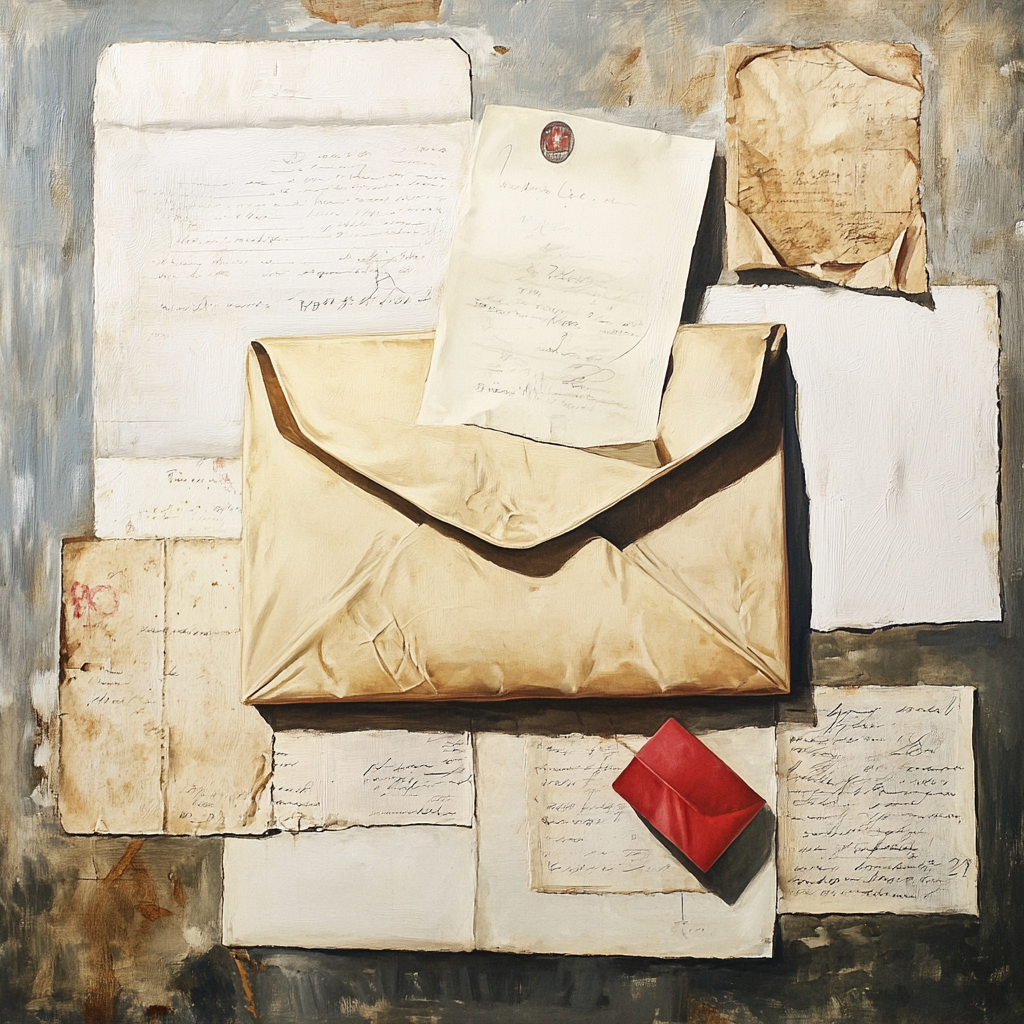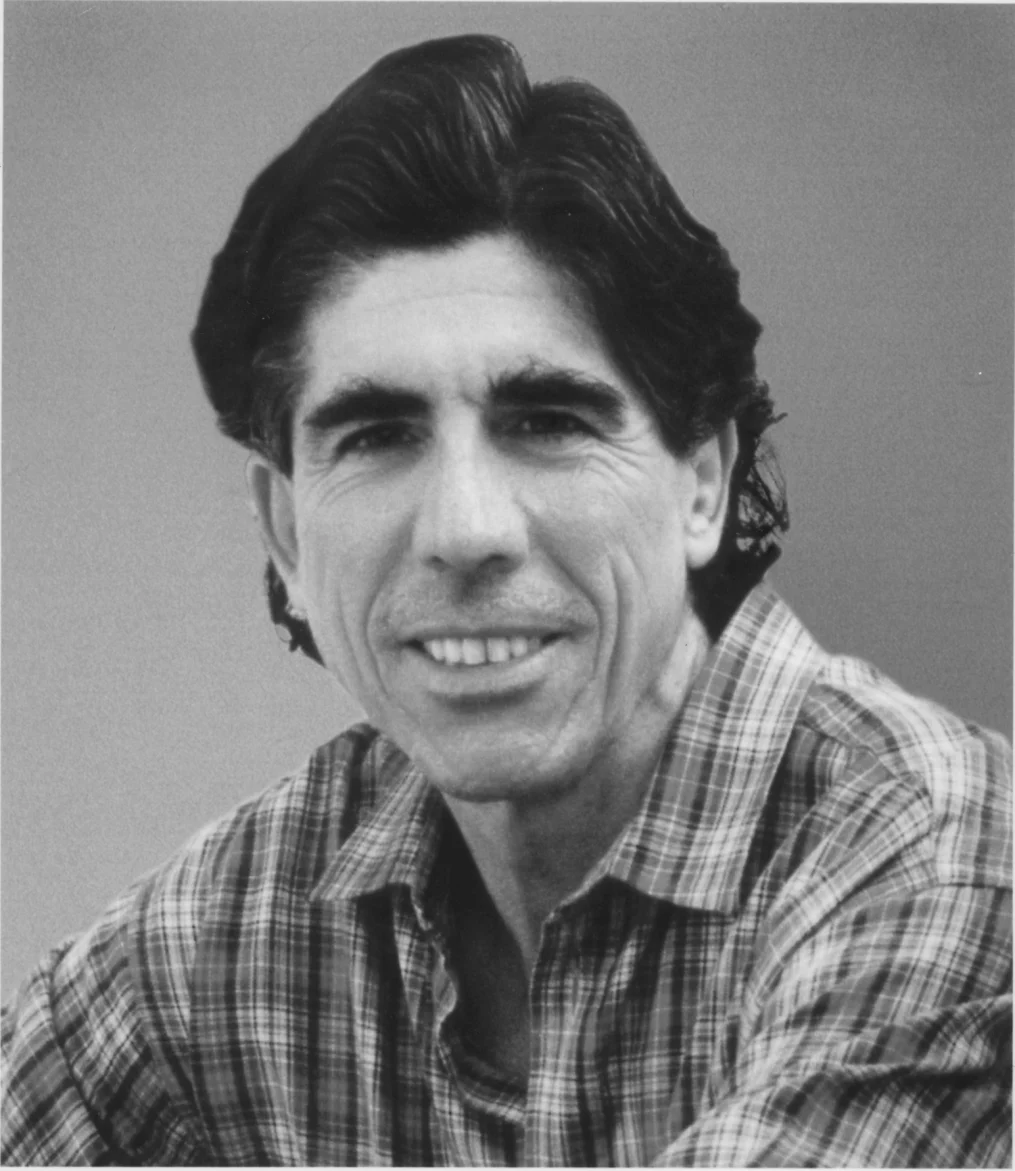勞瑞.芭金
此文刊登在《舊金山紀事報》
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張純如,《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書三十六歲的作者,十餘年來一直埋頭於1937年日軍侵佔南京大肆屠殺30萬同胞期間倖存者們所經歷的事件之中。最近,張純如採訪了巴丹死亡行軍( Bataan Death March)的倖存者。她在肯塔基州聽完倖存美軍講述的經歷後,因精神崩潰住院三天。回到灣區家中,儘管已服藥治療,她還是在十一月九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同情耗竭,繼發性創傷,替代性創傷。這些術語常常被用來描述像張純如這樣富有同情心的人在見證了人對人所施加的非人暴行後精神迷失的狀態。做了五年精神創傷科心理護理諮詢師後,我開始噩夢不斷、胸悶氣短,對孩子安全問題的恐懼與日俱增。於是我參加了一個心理創傷論壇,在那裡我第一次聽到“替代性創傷”這個術語。我開始對自己的症狀有所理解並且知道有必要停下工作去休假了。
心理創傷專家用「劑量」一詞來指涉創傷性事件暴露在當事人面前的衝擊程度。心理創傷方面的研究的新近發展讓我們可以描述人類大腦因心理創傷而產生的種種變化。甚至是次級暴露,特別是像張純如那樣經長時間累積的強大劑量衝擊,是會對大腦造成顯著的改變。警察、消防救火人員、心理治療師、記者和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也都是高危人群。
有些治療方案是可行的。在出現症狀前採取行動的話效果更好。治療方案包括友好互助的工作環境、和諧的家庭、有規律地鍛煉身體,在工作與娛樂之間取得平衡,同時有空和朋友——特別是能讓你開懷大笑的朋友——共度時光。
悼念張純如的人們都說她是那種「對他人之痛感同身受」而且「不知疲倦、使命必達」的人。也有人說,「對純如而言,沒有辦不到的事兒。」也許正因為如此,面對我們這個世界中的邪惡現實,張純如為了能夠改變它殞身不殆。我可以想像,那些冤魂的哀鳴是如何令她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每一個倖存者的經歷是如何令她愈陷愈深;為了將深淵般的痛苦呈現為文字,她是如何讓自己承擔那難以承擔的巨痛;她是如何肩負他人所經歷的苦難以求得我們能夠吸取教訓成為更好的人。
唯一的問題是,我們不願傾聽。我們不想聽,不願相信。傾訴內心的感受在這個國家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件窘事。我們甚至讓他們吃藥或者把他們灌醉也不願意敞開心扉。我們沒有學過如何關照他人的情感需求。當我們認識的人表達痛苦或悲傷時我們心裡難受。我們會迴避這種情境,因為我們擔心會說錯話或者自己在情感上變得手足無措。但是認可、關懷和安慰正是那些見證者所需要的。有時,哪怕是滿懷愛意的家人和忠實的朋友也不足以將深陷於他人之痛的人們解救出來。
張純如的一生照亮了許多人的生命,卻也在這一過程中讓自己的生命之光殞滅。與那些在 9.11 恐怖攻擊後趕往現場的消防員一樣,她不眠不休在這場悲劇的廢墟中忘我地篩查搜索。我們需要培育像她這樣不顧自我歸宿,將生命投入到追求真相的事業之中的人。我們必須讓埋頭於工作的他們有喘息之機,給予他們以讚美,傾聽他們的心聲,在他們快被絕望的深淵吞噬時把他們拽回來。
勞瑞‧芭金,臨床心理科專科護理師,正從事撰寫有關身心創傷倖存者的著作。
- (簡淑惠, 馬海寧合譯)